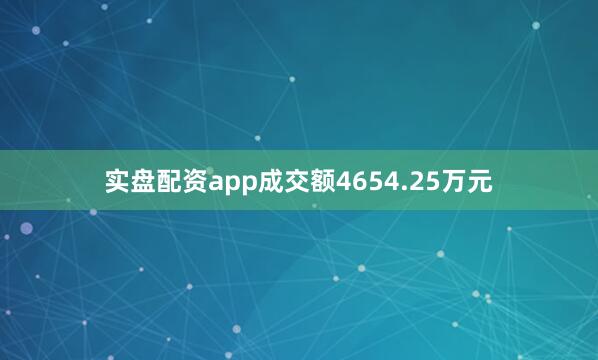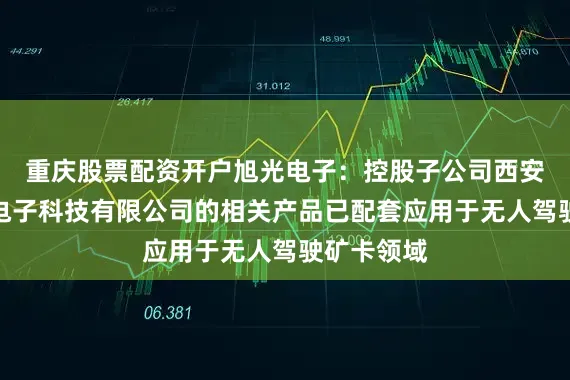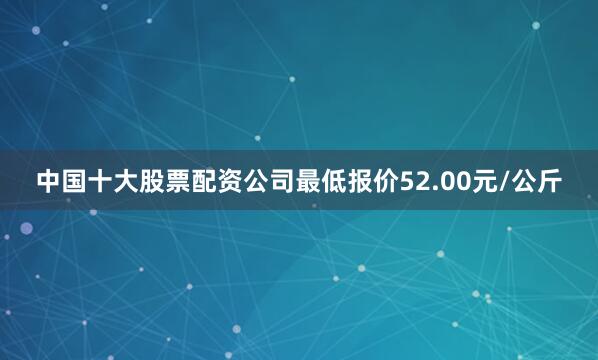嘉靖三十四年(公元1555年)正月22日深夜,京城诏狱里一间昏暗潮湿的牢房中,一名瘦削的中年男子正斜倚着冰冷的墙壁,盘腿而坐。
他神色坚毅,面容因病与杖刑而浮肿,眼中却无一丝怯意。他的手里握着一双被劈开的竹筷,筷子前端牢牢绑着一片尖锐的碎茶壶残片。
他咬着牙,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,伴随着每一次敲击,那锋利的碎茶壶残片便缓缓刺入他已然肿胀淤青的右腿深处,脓血喷涌而出,室内弥漫着腐败的血腥气。
这些物件的来历极为特殊:竹筷,是狱卒孙儒所赠;缠绑瓷片的丝线,是狱友何成从衣服上撕下;破碎茶壶出自牢头刘时守送来的一壶“好心”茶。没有药,没有酒精,没有麻药,他只能靠自己的意志力完成这一切。
这不是小说,也不是传说,而是清清楚楚记载在一位明代官员的自书年谱中。他叫杨继盛,一个真正将“忠臣”二字刻入骨血的谏臣。
展开剩余86%我们就从头讲起。
杨继盛,字仲芳,号椒山,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人,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容城县北河照村。他出身贫寒,自幼家道中落,父母失和,兄弟反目。早年丧母,兄嫂对他苛刻异常,甚至在他被贬之际以砖石相加。童年时的他只能靠在村塾外偷听讲学,一边放牛一边背书,一切皆靠自学苦读。
嘉靖二十六年(1547年),36岁的杨继盛高中进士,殿试列二甲十一名,等于全国第十四名,已属难得。朝廷授其为南京吏部主事,三年后调回北京,出任兵部车驾司主事。
本是青云直上之时,杨继盛却选择了另一条充满荆棘的路。
这一年,鞑靼人再度南下犯边。朝中重臣仇鸾上疏请皇帝开放马市,与蒙古进行贸易,以换取和平。他的逻辑很简单:打仗太贵,不如做生意,既减少冲突,又可赚取利润。
杨继盛却极力反对。他援引明初瓦剌入寇之例,列举四条理由:其一,蒙古所售多为劣马,无实用价值;其二,贸易为幌子,强奸抢掠为实;其三,开放马市将示弱于敌,滋长对方野心;其四,朝廷无法监管市舶,百姓将首当其害。
这份奏疏言辞激烈,掷地有声。嘉靖帝虽为之一动,但终抵不过仇鸾之言。结果,弹劾者下狱,贬官发配,杨继盛被贬至狄道(今甘肃临洮)为典史,连从九品也不是。
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沉沦,也为他后来再次起身埋下伏笔。
嘉靖三十一年(1552年),形势再变。边患依旧频繁,仇鸾之策毫无成效。嘉靖皇帝这才意识到,杨继盛当年的上疏或许才是真言。于是数次下诏,破格提拔。
一年内,他从无品典史升为真定知县,又接连任南京户部主事、刑部员外郎,最终调入京师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。这个职位掌握着全国武官的任命与升迁,是京官中的肥差之一。
这次升迁的背后,恰恰是权相严嵩的安排。仇鸾虽曾为严党核心,但因不懂权谋、屡自其道,已失去严嵩信任,被严徐联合弹劾,死后甚至被剖棺戮尸,枭首边疆。
严嵩希望借重杨继盛之名笼络人心,岂料却引狼入室。
杨继盛抵京仅两日,便向皇帝上呈奏疏——《请诛贼臣疏》。在这份奏折中,他历数严嵩十大罪状,请求将其问罪。文末言明:若所述不实,愿以死谢罪。
朝堂哗然,百官震惊。
此时的严嵩,权倾朝野,徐阶尚处韬光养晦之际,整个朝廷几乎是严党天下。在这种局势下敢于上谏,无异于自取灭亡。
更甚者,杨继盛还连带批评了大学士徐阶,指出其“每事依违,不敢持正,负国也”,彻底撕破了任何党派遮掩。
结果不难预料,三日之内,他被镇抚司逮捕入狱。
嘉靖帝震怒,并非仅因奏本,而是奏中一句话:
“皇上或问二王,令其面陈嵩恶。”所谓“二王”,指的是嘉靖仅存的两个皇子——裕王朱载坖与景王朱载圳。嘉靖信道,曾得道士言“二龙不得相见”,自此对皇子格外忌惮,从未立太子。
此话一出,皇帝以为杨继盛或受二王授意,愈发忌惮。
虽然狱中解释最终打消了皇帝疑虑,但死谏已成事实,严党之怒岂容轻饶?嘉靖帝下令杖责一百,并令刑部“从重议处”。
这本就是变相的处决——在正常情况下,一百杖已足以致命。
执行时,有人送酒解痛,有人披衣遮伤,但一杖杖打下去,杨继盛终究昏死过去。两腿溃烂,肿胀难行,只得由人搀扶回牢。
按理说,朝廷命官应入“官监”,但他却被安排至条件最差的“民监”,又遭“善意”的茶水毒害,双腿迅速腐烂。
于是便有了他用筷子碎瓷自行割肉放脓的一幕。
在狱中,虽有严党环伺,但亦不乏援手。
御史张弘斋、秀才侯冕、太监赵用、同僚王西石等人轮番送药送食,提牢官丘秉文更是将他悄悄转移到稍为干净的小屋中。
尽管腐肉两碗,流脓不止,他却奇迹般撑过了两年。
而与此同时,外界也在暗流涌动。
嘉靖帝始终未在杨继盛的死刑奏本上“勾决”——这是古代决定生死的最后一笔。
第一年没勾,第二年仍不勾,似乎在犹豫,也似乎在试探。
严嵩见风向微妙,竟一度准备为杨继盛求情,以平民愤。严党震惊,群起反对,鄢懋卿言:
“徐阶得意门生,一旦当国,继盛必辅之。我辈无遗类也,养虎自遗患耳!”
连严世蕃、袁应枢等也跪求阻止。最终严嵩决定,不再犹豫,直接斩草除根。
这一年,另一位重臣张经也因抗倭不力被严党赵文华诬陷。
在张经的死刑判决书上,严嵩悄然加上杨继盛的名字。
嘉靖帝看见张经,随手批示“依律处决”,未察觉其后藏有另一人名。
杨继盛,终以“诈传亲王令旨”之罪名被处死。
行刑前,他留下一首绝笔诗:
浩气还太虚,丹心照千古。 生平未报国,留作忠魂补。这一年,他47岁。
在他入狱的日子里,家乡保定巡抚艾希淳、御史徐绅等人凑银两为他置地三顷,为其家眷谋得安身之处。
其妻张氏曾上书请以死代夫,被严嵩扣压后自缢殉夫。
好友王遴在其被捕后曾许婚于杨之次子杨应箕,为其子孙谋得立身之基。
杨继盛死后,由史朝宾、王遴等人收尸安葬,忠魂得以归乡。
杨继盛不是徐阶的门生,更非党争工具。他与后来死谏的海瑞一样,皆是寒门出身,自幼受尽冷眼,以性命报国,以热血守道。
他死后七年,严嵩倒台,严党覆灭,徐阶登相,天下始知椒山之忠,忠臣之骨。
世人评价他:“烈丈夫,士之师表也。”
那么,问题回到最初:杨继盛明知弹劾严嵩凶多吉少,为何仍要一意孤行,视死如归?
也许,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,只为那一腔未酬的报国之志。
他说过:“荷国厚恩,欲思舍身图报,无下手得力处。”
这一次,他终于找到了“下手得力之处”。
——以死谏,撼奸臣,以生命点燃历史的正义之光。
发布于:广东省广升网-配资股票开户-如何股票配资-股票10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正规炒股杠杆平台是唯一一个需要冬眠的犬科动物
- 下一篇:没有了